以“余”留白当为“裕”
搬砖老湿机 好文天地 2022.03.21
陶渊明曾言:“勤靡余劳,心有常闲”。其意为勤勉耕耘,不遗余力,心中却常常有闲情逸致。如今物欲横流的浪潮翻涌不断,拥挤和喧嚣已成常态。既知急景流年都一瞬,何必困在现实的泥溷中裹挟着打转?人生最难得的,是敢于从泥沼中昂起头来喘气。且让这浮生半日的留白,为人生画卷着色。
以“余”留白,并非消磨时光,它所映衬出的,反而是惜时的智慧,闲适的美好,是用闲暇去为匆匆而逝的光阴作注解。我们往往在饮醉人生之酒后,才渴求那如品清茗的闲暇。

梁秋实说“人类最高理想,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,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,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,去享受人的生活。”古有汉代董遇以“三余之说”勤勉治学,读书百遍,其义自见;今有齐白石老人以“三鱼”妙解“三余”,以积极心态发现闲暇之美。
“手脚相当闲,头脑才能相当地忙起来”。换言之,巧度闲暇,亦是对我们灵魂的修炼。
以“余”留白,是从零零碎碎的闲暇之中,拼凑出完整的空地,以勤勉惜时的耕耘,开天辟地。数学家陈景润惜时如金,把一天24小时的分分秒秒都充分利用起来,即使在路上时,也不忘读读背背;鲁迅先生“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用在写作上”,一生著作颇丰,成为一代文坛巨匠;巴尔扎克每天如痴如狂地奋笔疾书,即使累得手臂疼痛,双眼流泪,也不肯浪费一刻碎片的时间,留下了那部深受喜爱的巨著《人间喜剧》。
可见,拥有海洋一般的充裕时间可以利用固然令人羡慕,然而能从海绵中挤出水来付诸行动更加令人敬佩。所谓“志士惜年,贤人惜日,圣人惜时”,“余”之力量,就是让看似无用的留白,汇聚而成行动上的“裕”之大用。
以“余”留白,是放慢脚步,欣赏风景,以一颗悠然之心自得其乐。它是辛弃疾放歌高唱“钟鼎山林都是梦,人间宠辱休惊。只消闲处遇平生”的宁静淡泊;是李易安“枕上诗书闲处好,门前风景雨来佳。”的恬淡悠闲;是汪曾祺“在黑白里温柔地爱着彩色,在彩色里朝圣黑白”的希望与热忱。
木心曾在《素履之往》中感慨道,“有时,人生真不去一句陶渊明。”的确,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之中,我们往往被纷繁的工作牵着鼻子走,像一只终日拉磨的疲惫的驴,这时,片刻的闲暇就显得尤为重要。“余”之力量,就是自守心田,以清欢的态度,凝结成思想上的“裕”之丰盈。
然而,一切没有灵魂参与的闲暇,都只是在低质量地消度光阴。闲暇不是所谓的“躺平”,不是一个人独自面对电视机直至头昏脑涨地睡去,不是用娱乐手段去令大脑感觉愉悦。
以“余”留白之所以不至于流于肤浅,就在于它有思想的打磨,有价值的沉淀。比起那些践踏光阴、消沉度日的人,我们更愿意在“余”中,读一本诗书,赏一幅名画,悟一个哲理。可见,如何度“余”,恰恰反映出人的精神品级与状态。此之,方可为“余”之真谛所在。
“江山风月,本无常主,闲时便是主人”,以“余”留白,做闲暇之主人,方可收获学问与真理之“裕”,闲适与幸福之“裕”,思想与灵魂之“裕”。(文/烧雪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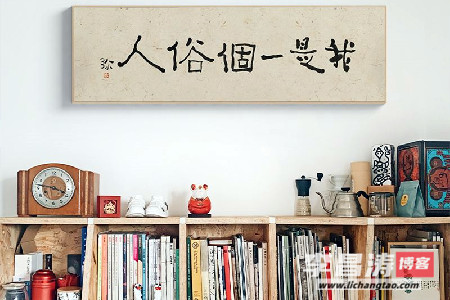




 赣ICP备18014042号
赣ICP备18014042号 赣公网安备 36031302000132号
赣公网安备 36031302000132号